温度夜读|多彩蛋袋过重五
(本文转自《温州新闻》 作者杨国华(驾20班))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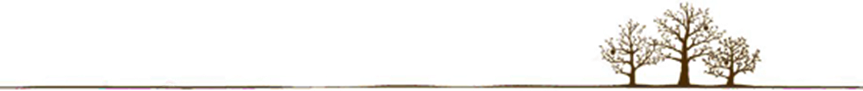
儿时过重五节,除了吃粽子,父亲在白酒中放少许雄黄,给我们的额头、手心、肚脐眼涂上雄黄酒之外,母亲必定给我们每个人煮一个鸡蛋,装在多彩蛋袋里,挂在胸口前。

多彩蛋袋是母亲灵巧的双手编织出来的。她坐在老屋的窗口下,用织毛线衣剩余下各种色彩的线头,5根一束,自底部束扎,系在窗框上,光阴在她身上缓缓流淌,灵巧的手指在不停地舞动,向上相互打结成网,到了顶端慢慢收口,装上鸡蛋,拉紧即可。
聪颖心细的母亲,设想在每一节如能套上一小截细细的塑料管,蛋袋就会更美观结实,可那时生活在物资缺乏的七十年代,乡村里根本买不到细细的塑料管。母亲就与父亲商量,想办法从哪儿能弄到?
这可难不倒当教师的父亲,他找来旧的细电线,抽出铜芯,剪成相等长的小段,于是母亲就可在织蛋袋时在每一节之间套上塑料管了。可是电线塑料管只有红、绿两种颜色,母亲想有多彩的塑料管,让蛋袋更加漂亮。于是父亲拿了爷爷做纸扎用的油彩,把塑料管涂抹得五彩缤纷,这可让母亲喜欢了,她终于编织出了色彩斑斓的蛋袋。

蛋袋因为有了多彩塑料管的支撑,显得无与伦比的美观,且又厚重结实。有了这样的蛋袋搭配,“重五蛋”就如晨曦升起的太阳多彩艳丽,又如一颗熠熠生辉的明珠闪烁光芒。小小的我们兄妹三人神气十足,晃荡着胸前的“重五蛋”,迷倒了好多人。妹妹走到老街上,不时有人拦下她,拉过胸前的蛋袋,歪着头仔细观摩,啧啧赞叹,想学着做这样的蛋袋。
小伙伴们聚在一起要撞蛋,我如何也不拿出来碰撞,想着自己的鸡蛋万一给撞破,就得要吃了,今年的重五节再也无法在胸前挂着多彩的蛋袋,要再等到来年,心里有太多的不舍。

来年的重五节还没到来,于是就有邻居替母亲出主意,何不多做一些蛋袋拿到老街上去卖,可赚到一笔小钱。母亲与父亲商量,觉得这个办法很好,一家人靠父亲微薄的工资度日,如有一笔额外的收入,岂不高兴?可父亲犯愁了,那么多的细小旧电线可要到哪儿收集呢?
爷爷得知后,摸一摸光滑的脑袋,掳了掳长长的胡子,乐哈哈说,这可有什么难啊,我可以弄到比电线塑料管更好的管子,这事我帮你们解决。
母亲到供销社买来各种色彩的纱线,就等着爷爷的管子。可爷爷卖着关子说,不急,要等天晴了才行呢。那些日子刚好是梅雨天气,但我们知道爷爷一定有办法,等着天气放晴。

天空终于展开笑脸,阳光斜进了家门,母亲叫我去催爷爷做管子。
爷爷从道坛的麦秸堆抽出些细小结实的麦秆,用剪刀剪成一公分左右的管子,然后放在不同颜色的油彩里渗泡,放在太阳底下晒干,各种色彩的管子散发出亮丽鲜艳的光彩,母亲看到后笑逐颜开。
于是母亲每天坐在屋檐下,前面倒放着竹椅子,将一束5根长约一尺,颜色不同的纱线扎紧底部,系在竹椅子靠背上,每一个网节的丝线里再套上五颜六色的麦秆管子,底部还要束上十多根5公分左右的五彩丝线,可在胸前轻盈飘动。爷爷做的麦秆管子可以取之不尽,母亲叫教书回家的父亲,还有我和妹妹一起,帮她串起挂在脖子上那条线的麦秆管子,如彩色珍珠项链一般的贵气。
母亲大约做了二百多个多彩蛋袋,重五之前的农历四月廿九,恰好是我们萧江老街一年一度的传统会市,从来没有摆摊卖过东西的母亲羞涩万分,叫上我给她帮忙,硬着头皮在老菜场附近摆了个摊子,挂出蛋袋在售卖,每个卖1毛钱。路过的左邻右舍,也帮母亲吆喝叫卖,不到半天时间,都全部卖完了。

母亲虽然也没赚多少钱,可那一次的卖蛋袋,成了母亲一辈子最美好的回忆。那个重五节,乡村里,老街上,不时飘过母亲编织的蛋袋,我看到蛋袋里的“重五蛋”,特别的香甜,似乎散发着母亲温馨的气息。
后来,多彩蛋袋是我儿时过重五节一份执着的渴望,也成为我而今时而的思念。
如今的重五,已经不再愁吃了,也不再给孩子们煮蛋挂蛋袋。就是给他们煮蛋,也不一定爱吃,更没有相互撞蛋的游戏和乐趣。这一切也许只根植在我们的脑海里,成为挥之不去的记忆。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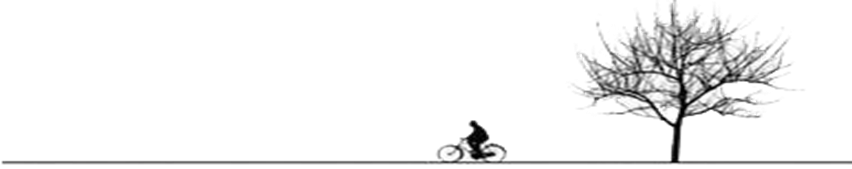
 官方微信
官方微信